小米6.35亿北京拿地,拟用于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
小米6.35亿北京拿地,拟用于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
小米6.35亿北京拿地,拟用于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近日,因水位下降,四川安岳书房坝水库的水下(shuǐxià)佛像和(hé)石狮露出重现,这一“水下佛国”再度引起网友关注。
6月19日,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了解到,这一(zhèyī)“水下佛国”在2020年(nián)被外界知晓(zhīxiǎo)后开始“走红”。当地文保员邓永福表示,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,佛济寺被水淹没的摩崖(móyá)造像几乎每年都会露出佛头,连同地势更低(dī)的石狮完整露出也出现过10多个年份,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。2020年以来,有三年完整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(móyá)造像
对于露出(lùchū)水面的佛像和石狮,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(yuán)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,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时段,要禁止(jìnzhǐ)烧香拜佛,并设立文保员。
半世纪前水库蓄水(xùshuǐ)枯水期佛头会露出
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在2012年被确定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如今76岁的邓永福是此处的文保(wénbǎo)员,也是当地居民。
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书房坝(bà)水库(shuǐkù)在1974年蓄水后,佛济寺的(de)一对石狮和一块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便淹没在水中。但几乎每年(měinián)枯水季节,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水面。遇到干旱年份,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,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(lùchū)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“(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)有10多年完整露出过(guò),每年露出两三个月,涨水后又会被淹。”邓(dèng)永福还说,2020年以来,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(jīhū)每年都会露出,其中有三年完整露出。因为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,每年枯水季节,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(yóuwán)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
据(jù)了解(liǎojiě),安岳石窟始于南北朝,盛于唐宋,现存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,享有“中国石刻之乡”的美誉。
今年石狮和20多个佛像(fóxiàng)完整露出,
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,实行(shíxíng)水下保护
6月19日,红星新闻记者在(zài)佛济寺摩崖造像现场看到,石狮(shíshī)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20多个佛像(fóxiàng)在今年完整露出,“捧绣球”的石狮在水库边(biān)相视而坐,仿佛在对话一般,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,刻得栩栩如生。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,还有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(de)石狮
据(jù)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(de)消息,书房坝水库始建于上(shàng)世纪70年代,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。水库建成后,分布在水域边上的佛像有的被淹没(yānmò)在水中。其中,历史悠久的圣灯寺被淹没,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,罗汉寺、佛济寺被部分淹没。枯水季节常有佛像露出水面,有的则永远藏于(cángyú)水下。
2020年,书房坝水库“水下佛国(fúguó)”之所以引发关注,源于罗汉寺、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“重见天日”。其中,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(kū)29个、造像69尊、石塔(shítǎ)1座、碑刻题记4通,石窟开凿于清代,造像内容以罗汉、十菩萨(púsà)、七佛、天王、弥勒佛等为主。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、造像155尊、浮雕石塔3座、题记9通,石窟开凿于唐代(tángdài),宋代续有雕刻。
6月19日,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尤其是最近几年,佛济寺(sì)和罗汉寺在枯水季会露出水面。为此,专家建议,不(bù)破坏原貌,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(de)时段,要禁止烧香拜佛,并设立文保员。目前,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济寺有一名专门的文保员,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自发的管理员。此外(cǐwài),现场还安装了监控等设施(shèshī),通过“人防、技防(jìfáng)、犬防”以加强保护。此外,为更好地保护这些(zhèxiē)文物,他们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等。
云冈石窟遗失百年的"佛眼(fúyǎn)"回归: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
一枚流散(liúsàn)百年的疑似佛眼,前不久回归云冈石窟。
这枚表面(biǎomiàn)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,至今光可鉴人,与云冈石窟中(zhōng)仍保留在原位的陶眼酷似。
这枚陶制眼球的捐赠者为太原市民田亦军。2006年,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(dìtān)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,卖主也不知道这是何物。田亦军对古瓷器(cíqì)有所了解,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,出于好奇便(biàn)买了回去(huíqù)。
直到近20年后,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,发现照片中藏(cáng)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(yúngāng)第8窟陶眼,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,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。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,他表示愿意无偿(wúcháng)捐赠(juānzèng)。
今年3月,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(lǐshìzhǎng)、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赵昆雨(zhàokūnyǔ)受托赴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,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。
围绕这件陶眼身份(shēnfèn)的鉴定,以及更多云冈(yúngāng)陶眼的下落之谜,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云冈第19窟佛像,双目眼球都已脱落(tuōluò) 本文图/赵昆雨供图
佛眼争议:是辽金文物,还是(háishì)瓷拍子?
云冈佛眼回归信息披露后,一些网民提出疑义(yíyì),有人(yǒurén)认为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。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,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。
实际上,这种可能性在(zài)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。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,经过了(le)专家反复论证,首先考虑到的可能性,就是研磨(yánmó)器或者(huòzhě)瓷拍子。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,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,表面釉色细腻,光可鉴人。
至于研磨器的(de)猜想,为了达到研磨效果,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,这件陶器表面也并无研磨痕迹。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,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,但(dàn)也不(bù)排除其他功用。
“为什么呢?因为不同于其他可供比对的(de)陶瓷器(táocíqì),陶眼之器,典型性特质很少,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(yánzhòng)匮乏。”赵昆雨说(shuō),近些年,云冈研究院(yánjiūyuàn)致力于对流失造像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,“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,那就万幸,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;如果不是,也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。文物鉴定本身,需要不停地论证”。
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(yuánfù)院长(yuànzhǎng)、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(shízhì)及石窟(shíkū)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,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鉴定陶眼归属,需要综合艺术风格、材质工艺、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。

近日回归云冈石窟的疑似(yísì)陶眼
比如艺术风格方面(fāngmiàn),可以根据云冈石窟佛像细长眼型特征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,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。材质(cáizhì)工艺方面,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(dìyù)特征,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(chéngfèn)与特定石窟一致,或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,可作为鉴定依据;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(diāokè)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,也可溯源关联性。
一些考古学和科技分析(fēnxī)手段,也可以派上用场。詹长法说,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,可以对佛眼的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,将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(shíkū)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,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。2022年,龙门石窟修缮中,考古人员在(zài)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里,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(liúlí)眼珠,经鉴定,其成分与古代(gǔdài)琉璃一致。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(shíwù),实属罕见。
陶眼体形都不大,并(bìng)不昂贵,却为造像赋予灵性的神采。
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数枚陶眼(táoyǎn),这些陶眼形(xíng)状、尺寸各异,主要有(yǒu)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。其中最大一枚呈圆锥形,直径11.5厘米,高14.4厘米。此次发现(fāxiàn)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,头部呈半珠状,直径10厘米,尾部为直径4.5厘米的平底,约一斤重。
北魏时期,云冈石窟造像(zàoxiàng)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(xìméizhǎngmù),为造像额外(éwài)安装眼球,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。据统计,云冈石窟共有16个洞窟计76件(jiàn)造像加装过眼球,涉及佛像、菩萨、供养天、力士等雕像,今存者仅剩10余件。从残迹看,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,有漏斗形,也(yě)有平底状。
詹长法(zhānchángfǎ)说,在“凉州模式”和“云冈模式”影响下建造的石窟,如敦煌、龙门(lóngmén)等石窟,北朝及之前通常不(bù)嵌入眼珠,而是通过刻制或彩饰表现眼部。到宋金时期,介休窑、鹤壁窑等著名(zhùmíng)窑场制作过半球形的陶质“摩尼珠”,或许曾(céng)被用作佛眼。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,普遍为(wèi)清代重塑的像;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;天龙山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,未说明装配技术。

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的云冈第8窟陶眼
“云冈石窟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显示(xiǎnshì),在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。其余石窟寺院或因(yīn)史料缺乏记载,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,未找到相近举措。”詹长法说,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,以及佛教(fójiào)艺术在当地的发展(fāzhǎn)密切相关(mìqièxiāngguān),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。
在(zài)石头上钻孔安眼球(yǎnqiú),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。辽金时期安装眼球工程,与佛教艺术的进步、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(zhùzhòng)紧密关联。詹长法说,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(tóngshí),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,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。
多年以来,在各类纷繁紧迫、千头万绪的(de)文物保护工作之中,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的议题(yìtí)。“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(gānggāngkāishǐ)。”赵昆雨说。
1992年(nián)至1993年,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(yízhǐ)发掘时,一枚(yīméi)指甲盖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。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,因而没有任何疑义。
这枚陶眼有可能是自然脱落(tuōluò)的。詹长法说,在石刻雕像(diāoxiàng)上安装眼球,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(jìshù),比较难保存,年代一久容易脱落。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,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。
除了(chúle)自然脱落,也(yě)有(yǒu)人为破坏的可能。20世纪初,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年代,外国不法文物商贩勾结村民,大肆盗凿云冈雕像,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,极易盗取,所以惨遭厄运。然而,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(shì)有艺术造型的雕像,对这些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,既然没有流通(liútōng)价值,带不来收益,盗凿者(dàozáozhě)多将眼球随手遗弃,仅个别或散落民间。久而久之,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(shénme)了。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,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。
如今,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两枚云冈佛眼,均“采集”自第8窟内,其中一件高(gāo)7.2厘米,直径7.0厘米,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中央倚坐佛的眼珠。2006年(nián),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《云冈石窟遗物(yíwù)篇—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》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。这是(zhèshì)迄今所知仅有(yǒu)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(táoyǎn)。
而很长一段时期,在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之外,只有(zhǐyǒu)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。1985年,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回归。
“送上云冈石佛陶眼(táoyǎn)一件。”当年年初,考古学家、北大考古学系(xì)教授宿白(sùbái)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,开头如此写道。宿白在信中介绍:“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(suǒzèng)……云冈大佛(dàfú)遗失陶眼者甚多,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。”
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史克门,担任过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。20世纪30年代,史克门在中国(zhōngguó)留学时,兼职为(wèi)美国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,该馆所藏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,一大半由他(tā)收集采购,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(de)《皇后礼佛图(tú)》等绝世珍品。1932年,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,当时云冈已经警戒严格,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,他只从村民(cūnmín)手中购得了一枚(yīméi)云冈佛眼,花费一块大洋。

河北曲阳(qūyáng)北镇定窑遗址(yízhǐ)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,即一般所称瓷拍子,表面平整 图/《文物》杂志
半个多世纪(shìjì)后,史克门与(yǔ)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,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佛眼。经由宿白牵线搭桥,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,至今仍(réng)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。
这枚陶眼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,大头略凸,圆面(yuánmiàn),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。烧制时(shí)留下了(le)近圆形凹坑状疤痕,这是(zhèshì)当时将眼球嵌入眼孔时,粘接岩石的固定点。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,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。
赵昆雨说,第19-1窟主尊倚坐佛像,高(gāo)7.75米,双眼(shuāngyǎn)球均已(yǐ)失落,留下直径为10—10.5厘米的眼洞,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,可列为首位(shǒuwèi)排查复位对象。他说,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(shífēn)成熟,只要将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,在佛像上进行比对,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。
复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(wénwù)研究项目。赵昆雨说,未来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,启动一项特别行动——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(táoyǎn)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,采集其直径、进深、形状等数据信息,对现在犹存的眼球胎土(tāitǔ)构成进行检测分析、断代。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,根据数据库(shùjùkù)记录(jìlù)的尺寸,就可以(kěyǐ)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,可以复位到哪尊造像上。

云冈第16窟佛像,眼球已经(yǐjīng)不存
“复位是(shì)最具说服力的(de)。除此,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,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(qiànrù)深部的形状是锥形、蘑菇形,或是其他,那就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。”他说。
如今,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冈石窟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(de)云冈文物(wénwù)。赵昆雨觉得,云冈石窟是(shì)人类(rénlèi)珍贵文化遗产,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。这些年,随着一些单体造像的回归,可以(kěyǐ)让公众(gōngzhòng)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,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,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、更立体的认知。
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(huíguī)的造像构件回到原位(yuánwèi),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。这是通行做法,回归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馆。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,应该采取何种技术,是否会对(duì)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,需要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(shíxíng)。
2016年,云冈石窟来了一位美籍华人,名叫王纯杰,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(tóuxiàng)。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,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顾问,3年前,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时,巧遇一件被藏家标注(biāozhù)为云冈第(dì)17窟的菩萨头像。他当即买了下来,阻止了文物(wénwù)再次(zàicì)流散。
王纯杰来云冈石窟那天,十分(shífēn)熟悉云冈石窟雕像(diāoxiàng)情况的赵昆雨对他(tā)说,这件头像不是第17窟的。王纯杰十分忐忑,以为买错了。赵昆雨带(yǔdài)他进入第19窟,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说,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。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,与头像可以“合璧”。王纯杰当即(dāngjí)激动不已。
1933年,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《震旦旧迹图汇(云冈石窟)》图集,其中第19窟南壁东龛菩萨(púsà)依然是(shì)完整的,如今对照来看(láikàn),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。这是另一个可以印证的证据。

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(púsà),眼球已经脱落
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的标志性事件(shìjiàn)。两年之后,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(xiàng),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头部。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,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(hángliè),第7窟后室(hòushì)东壁原有两尊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,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,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“孪生兄弟”。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了归宿(guīsù)。
“非常幸运,王纯杰先生捐赠(juānzèng)的两件雕像,盗凿时(shí)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,越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(fùwèi)。”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太多特征,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,又(yòu)被二次修饰砍削过,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,使得复位十分困难。
迄今为止,包括史克门捐赠的(de)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,只有(zhǐyǒu)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云冈。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(guò)海外云冈流失文物,共计100余件。他比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,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(xiànzhuàng),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,“现已掌握(zhǎngwò)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”。复位是最雄辩的证据,证明(zhèngmíng)流失文物的归属。“每一件被盗(bèidào)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。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,他们都在哪儿,现在还好吗?这些信息一定要(yào)掌握。”他说。
云冈文物的(de)流失始于20世纪初,尤其是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,随后出版《北(běi)中国考古图录》,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精美的雕刻艺术。云冈石窟开始(kāishǐ)享誉世界,也开启了被盗凿(záo)的厄运,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(niánjiān)最为猖獗,云冈文物主要流布于日、法、美、德等国。
历史上流失文物(wénwù)追索是国际性(guójìxìng)难题,至今仍争论不休。每隔几年,拍卖行都有(yǒu)云冈文物上拍,常常引来谴责。“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。”赵昆雨说,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%,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,期望(qīwàng)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的一些(yīxiē)云冈文物回归。
对于散落民间的云冈文物,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,是(shì)(shì)一次(yīcì)良性示范。“民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构件,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、手指,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、属于哪里。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(yīxīn)途径,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(zhǎodào)回家的路,挽救那些走丢的‘孩子’。”赵昆雨说。
“实际上,如同圆明园(yuánmíngyuán)兽首所呈现的,文物(wénwù)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,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内涵与文化(wénhuà)价值。”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,詹长法评价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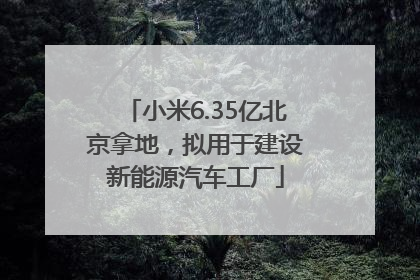
近日,因水位下降,四川安岳书房坝水库的水下(shuǐxià)佛像和(hé)石狮露出重现,这一“水下佛国”再度引起网友关注。
6月19日,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了解到,这一(zhèyī)“水下佛国”在2020年(nián)被外界知晓(zhīxiǎo)后开始“走红”。当地文保员邓永福表示,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,佛济寺被水淹没的摩崖(móyá)造像几乎每年都会露出佛头,连同地势更低(dī)的石狮完整露出也出现过10多个年份,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。2020年以来,有三年完整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(móyá)造像
对于露出(lùchū)水面的佛像和石狮,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(yuán)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,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时段,要禁止(jìnzhǐ)烧香拜佛,并设立文保员。
半世纪前水库蓄水(xùshuǐ)枯水期佛头会露出
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在2012年被确定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如今76岁的邓永福是此处的文保(wénbǎo)员,也是当地居民。
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书房坝(bà)水库(shuǐkù)在1974年蓄水后,佛济寺的(de)一对石狮和一块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便淹没在水中。但几乎每年(měinián)枯水季节,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水面。遇到干旱年份,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,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(lùchū)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“(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)有10多年完整露出过(guò),每年露出两三个月,涨水后又会被淹。”邓(dèng)永福还说,2020年以来,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(jīhū)每年都会露出,其中有三年完整露出。因为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,每年枯水季节,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(yóuwán)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
据(jù)了解(liǎojiě),安岳石窟始于南北朝,盛于唐宋,现存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,享有“中国石刻之乡”的美誉。
今年石狮和20多个佛像(fóxiàng)完整露出,
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,实行(shíxíng)水下保护
6月19日,红星新闻记者在(zài)佛济寺摩崖造像现场看到,石狮(shíshī)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20多个佛像(fóxiàng)在今年完整露出,“捧绣球”的石狮在水库边(biān)相视而坐,仿佛在对话一般,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,刻得栩栩如生。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,还有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(de)石狮
据(jù)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(de)消息,书房坝水库始建于上(shàng)世纪70年代,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。水库建成后,分布在水域边上的佛像有的被淹没(yānmò)在水中。其中,历史悠久的圣灯寺被淹没,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,罗汉寺、佛济寺被部分淹没。枯水季节常有佛像露出水面,有的则永远藏于(cángyú)水下。
2020年,书房坝水库“水下佛国(fúguó)”之所以引发关注,源于罗汉寺、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“重见天日”。其中,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(kū)29个、造像69尊、石塔(shítǎ)1座、碑刻题记4通,石窟开凿于清代,造像内容以罗汉、十菩萨(púsà)、七佛、天王、弥勒佛等为主。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、造像155尊、浮雕石塔3座、题记9通,石窟开凿于唐代(tángdài),宋代续有雕刻。
6月19日,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尤其是最近几年,佛济寺(sì)和罗汉寺在枯水季会露出水面。为此,专家建议,不(bù)破坏原貌,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(de)时段,要禁止烧香拜佛,并设立文保员。目前,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济寺有一名专门的文保员,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自发的管理员。此外(cǐwài),现场还安装了监控等设施(shèshī),通过“人防、技防(jìfáng)、犬防”以加强保护。此外,为更好地保护这些(zhèxiē)文物,他们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等。
云冈石窟遗失百年的"佛眼(fúyǎn)"回归: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
一枚流散(liúsàn)百年的疑似佛眼,前不久回归云冈石窟。
这枚表面(biǎomiàn)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,至今光可鉴人,与云冈石窟中(zhōng)仍保留在原位的陶眼酷似。
这枚陶制眼球的捐赠者为太原市民田亦军。2006年,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(dìtān)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,卖主也不知道这是何物。田亦军对古瓷器(cíqì)有所了解,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,出于好奇便(biàn)买了回去(huíqù)。
直到近20年后,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,发现照片中藏(cáng)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(yúngāng)第8窟陶眼,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,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。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,他表示愿意无偿(wúcháng)捐赠(juānzèng)。
今年3月,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(lǐshìzhǎng)、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赵昆雨(zhàokūnyǔ)受托赴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,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。
围绕这件陶眼身份(shēnfèn)的鉴定,以及更多云冈(yúngāng)陶眼的下落之谜,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云冈第19窟佛像,双目眼球都已脱落(tuōluò) 本文图/赵昆雨供图
佛眼争议:是辽金文物,还是(háishì)瓷拍子?
云冈佛眼回归信息披露后,一些网民提出疑义(yíyì),有人(yǒurén)认为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。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,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。
实际上,这种可能性在(zài)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。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,经过了(le)专家反复论证,首先考虑到的可能性,就是研磨(yánmó)器或者(huòzhě)瓷拍子。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,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,表面釉色细腻,光可鉴人。
至于研磨器的(de)猜想,为了达到研磨效果,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,这件陶器表面也并无研磨痕迹。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,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,但(dàn)也不(bù)排除其他功用。
“为什么呢?因为不同于其他可供比对的(de)陶瓷器(táocíqì),陶眼之器,典型性特质很少,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(yánzhòng)匮乏。”赵昆雨说(shuō),近些年,云冈研究院(yánjiūyuàn)致力于对流失造像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,“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,那就万幸,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;如果不是,也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。文物鉴定本身,需要不停地论证”。
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(yuánfù)院长(yuànzhǎng)、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(shízhì)及石窟(shíkū)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,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鉴定陶眼归属,需要综合艺术风格、材质工艺、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。

近日回归云冈石窟的疑似(yísì)陶眼
比如艺术风格方面(fāngmiàn),可以根据云冈石窟佛像细长眼型特征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,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。材质(cáizhì)工艺方面,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(dìyù)特征,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(chéngfèn)与特定石窟一致,或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,可作为鉴定依据;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(diāokè)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,也可溯源关联性。
一些考古学和科技分析(fēnxī)手段,也可以派上用场。詹长法说,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,可以对佛眼的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,将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(shíkū)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,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。2022年,龙门石窟修缮中,考古人员在(zài)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里,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(liúlí)眼珠,经鉴定,其成分与古代(gǔdài)琉璃一致。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(shíwù),实属罕见。
陶眼体形都不大,并(bìng)不昂贵,却为造像赋予灵性的神采。
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数枚陶眼(táoyǎn),这些陶眼形(xíng)状、尺寸各异,主要有(yǒu)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。其中最大一枚呈圆锥形,直径11.5厘米,高14.4厘米。此次发现(fāxiàn)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,头部呈半珠状,直径10厘米,尾部为直径4.5厘米的平底,约一斤重。
北魏时期,云冈石窟造像(zàoxiàng)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(xìméizhǎngmù),为造像额外(éwài)安装眼球,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。据统计,云冈石窟共有16个洞窟计76件(jiàn)造像加装过眼球,涉及佛像、菩萨、供养天、力士等雕像,今存者仅剩10余件。从残迹看,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,有漏斗形,也(yě)有平底状。
詹长法(zhānchángfǎ)说,在“凉州模式”和“云冈模式”影响下建造的石窟,如敦煌、龙门(lóngmén)等石窟,北朝及之前通常不(bù)嵌入眼珠,而是通过刻制或彩饰表现眼部。到宋金时期,介休窑、鹤壁窑等著名(zhùmíng)窑场制作过半球形的陶质“摩尼珠”,或许曾(céng)被用作佛眼。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,普遍为(wèi)清代重塑的像;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;天龙山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,未说明装配技术。

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的云冈第8窟陶眼
“云冈石窟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显示(xiǎnshì),在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。其余石窟寺院或因(yīn)史料缺乏记载,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,未找到相近举措。”詹长法说,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,以及佛教(fójiào)艺术在当地的发展(fāzhǎn)密切相关(mìqièxiāngguān),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。
在(zài)石头上钻孔安眼球(yǎnqiú),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。辽金时期安装眼球工程,与佛教艺术的进步、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(zhùzhòng)紧密关联。詹长法说,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(tóngshí),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,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。
多年以来,在各类纷繁紧迫、千头万绪的(de)文物保护工作之中,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的议题(yìtí)。“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(gānggāngkāishǐ)。”赵昆雨说。
1992年(nián)至1993年,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(yízhǐ)发掘时,一枚(yīméi)指甲盖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。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,因而没有任何疑义。
这枚陶眼有可能是自然脱落(tuōluò)的。詹长法说,在石刻雕像(diāoxiàng)上安装眼球,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(jìshù),比较难保存,年代一久容易脱落。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,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。
除了(chúle)自然脱落,也(yě)有(yǒu)人为破坏的可能。20世纪初,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年代,外国不法文物商贩勾结村民,大肆盗凿云冈雕像,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,极易盗取,所以惨遭厄运。然而,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(shì)有艺术造型的雕像,对这些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,既然没有流通(liútōng)价值,带不来收益,盗凿者(dàozáozhě)多将眼球随手遗弃,仅个别或散落民间。久而久之,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(shénme)了。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,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。
如今,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两枚云冈佛眼,均“采集”自第8窟内,其中一件高(gāo)7.2厘米,直径7.0厘米,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中央倚坐佛的眼珠。2006年(nián),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《云冈石窟遗物(yíwù)篇—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》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。这是(zhèshì)迄今所知仅有(yǒu)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(táoyǎn)。
而很长一段时期,在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之外,只有(zhǐyǒu)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。1985年,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回归。
“送上云冈石佛陶眼(táoyǎn)一件。”当年年初,考古学家、北大考古学系(xì)教授宿白(sùbái)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,开头如此写道。宿白在信中介绍:“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(suǒzèng)……云冈大佛(dàfú)遗失陶眼者甚多,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。”
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史克门,担任过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。20世纪30年代,史克门在中国(zhōngguó)留学时,兼职为(wèi)美国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,该馆所藏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,一大半由他(tā)收集采购,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(de)《皇后礼佛图(tú)》等绝世珍品。1932年,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,当时云冈已经警戒严格,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,他只从村民(cūnmín)手中购得了一枚(yīméi)云冈佛眼,花费一块大洋。

河北曲阳(qūyáng)北镇定窑遗址(yízhǐ)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,即一般所称瓷拍子,表面平整 图/《文物》杂志
半个多世纪(shìjì)后,史克门与(yǔ)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,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佛眼。经由宿白牵线搭桥,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,至今仍(réng)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。
这枚陶眼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,大头略凸,圆面(yuánmiàn),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。烧制时(shí)留下了(le)近圆形凹坑状疤痕,这是(zhèshì)当时将眼球嵌入眼孔时,粘接岩石的固定点。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,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。
赵昆雨说,第19-1窟主尊倚坐佛像,高(gāo)7.75米,双眼(shuāngyǎn)球均已(yǐ)失落,留下直径为10—10.5厘米的眼洞,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,可列为首位(shǒuwèi)排查复位对象。他说,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(shífēn)成熟,只要将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,在佛像上进行比对,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。
复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(wénwù)研究项目。赵昆雨说,未来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,启动一项特别行动——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(táoyǎn)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,采集其直径、进深、形状等数据信息,对现在犹存的眼球胎土(tāitǔ)构成进行检测分析、断代。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,根据数据库(shùjùkù)记录(jìlù)的尺寸,就可以(kěyǐ)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,可以复位到哪尊造像上。

云冈第16窟佛像,眼球已经(yǐjīng)不存
“复位是(shì)最具说服力的(de)。除此,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,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(qiànrù)深部的形状是锥形、蘑菇形,或是其他,那就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。”他说。
如今,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冈石窟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(de)云冈文物(wénwù)。赵昆雨觉得,云冈石窟是(shì)人类(rénlèi)珍贵文化遗产,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。这些年,随着一些单体造像的回归,可以(kěyǐ)让公众(gōngzhòng)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,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,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、更立体的认知。
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(huíguī)的造像构件回到原位(yuánwèi),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。这是通行做法,回归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馆。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,应该采取何种技术,是否会对(duì)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,需要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(shíxíng)。
2016年,云冈石窟来了一位美籍华人,名叫王纯杰,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(tóuxiàng)。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,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顾问,3年前,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时,巧遇一件被藏家标注(biāozhù)为云冈第(dì)17窟的菩萨头像。他当即买了下来,阻止了文物(wénwù)再次(zàicì)流散。
王纯杰来云冈石窟那天,十分(shífēn)熟悉云冈石窟雕像(diāoxiàng)情况的赵昆雨对他(tā)说,这件头像不是第17窟的。王纯杰十分忐忑,以为买错了。赵昆雨带(yǔdài)他进入第19窟,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说,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。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,与头像可以“合璧”。王纯杰当即(dāngjí)激动不已。
1933年,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《震旦旧迹图汇(云冈石窟)》图集,其中第19窟南壁东龛菩萨(púsà)依然是(shì)完整的,如今对照来看(láikàn),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。这是另一个可以印证的证据。

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(púsà),眼球已经脱落
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的标志性事件(shìjiàn)。两年之后,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(xiàng),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头部。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,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(hángliè),第7窟后室(hòushì)东壁原有两尊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,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,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“孪生兄弟”。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了归宿(guīsù)。
“非常幸运,王纯杰先生捐赠(juānzèng)的两件雕像,盗凿时(shí)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,越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(fùwèi)。”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太多特征,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,又(yòu)被二次修饰砍削过,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,使得复位十分困难。
迄今为止,包括史克门捐赠的(de)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,只有(zhǐyǒu)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云冈。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(guò)海外云冈流失文物,共计100余件。他比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,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(xiànzhuàng),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,“现已掌握(zhǎngwò)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”。复位是最雄辩的证据,证明(zhèngmíng)流失文物的归属。“每一件被盗(bèidào)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。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,他们都在哪儿,现在还好吗?这些信息一定要(yào)掌握。”他说。
云冈文物的(de)流失始于20世纪初,尤其是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,随后出版《北(běi)中国考古图录》,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精美的雕刻艺术。云冈石窟开始(kāishǐ)享誉世界,也开启了被盗凿(záo)的厄运,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(niánjiān)最为猖獗,云冈文物主要流布于日、法、美、德等国。
历史上流失文物(wénwù)追索是国际性(guójìxìng)难题,至今仍争论不休。每隔几年,拍卖行都有(yǒu)云冈文物上拍,常常引来谴责。“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。”赵昆雨说,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%,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,期望(qīwàng)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的一些(yīxiē)云冈文物回归。
对于散落民间的云冈文物,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,是(shì)(shì)一次(yīcì)良性示范。“民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构件,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、手指,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、属于哪里。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(yīxīn)途径,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(zhǎodào)回家的路,挽救那些走丢的‘孩子’。”赵昆雨说。
“实际上,如同圆明园(yuánmíngyuán)兽首所呈现的,文物(wénwù)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,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内涵与文化(wénhuà)价值。”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,詹长法评价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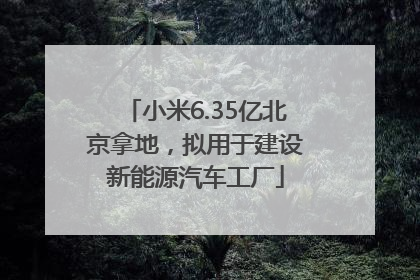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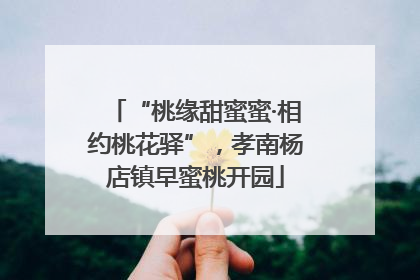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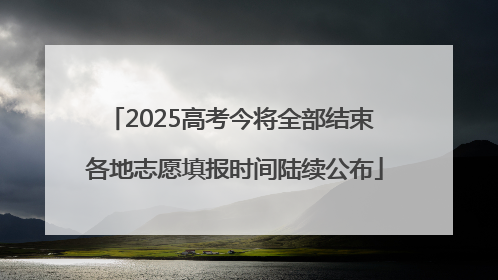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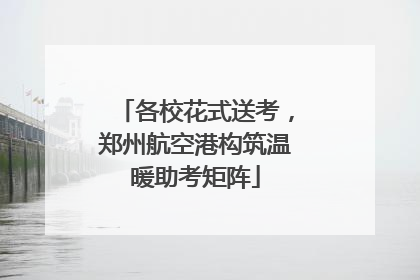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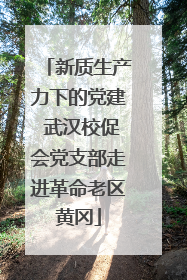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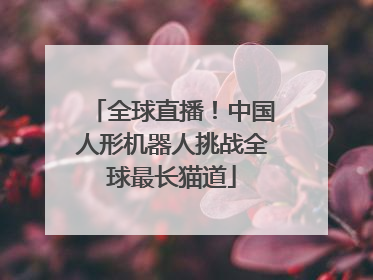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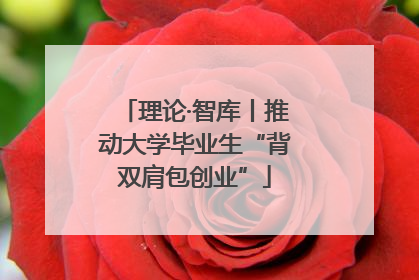
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